0
留言稍后联系!

發布時間:2020-03-03所屬分類:園林工程師瀏覽:1448次
摘 要: 摘 要 文人園林的審美是古典園林研究的重要問題。在傳統文化的熏陶下,我們強調對文人園林的詩性感悟和外形模仿,缺乏對園林審美本質的追問。本文運用格式塔心理學整體論和同型論的觀點,從園林主題、造園手法和園林題詠方面分析文人園林網師園的審美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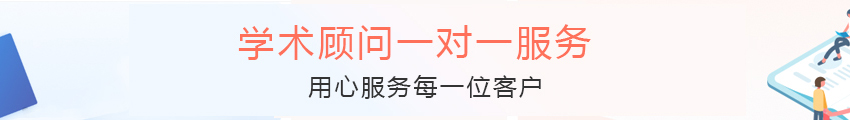
摘 要 文人園林的審美是古典園林研究的重要問題。在傳統文化的熏陶下,我們強調對文人園林的詩性感悟和外形模仿,缺乏對園林審美本質的追問。本文運用格式塔心理學整體論和同型論的觀點,從園林主題、造園手法和園林題詠方面分析文人園林網師園的審美特點,認為園的主題的確立與消隱是審美心物場逐漸轉變的外在表現;造園手法是知覺組織原則的綜合應用;園林題詠喚起了“心”與“物”的同型,營造了豐富的景觀意象,促使著審美經驗的完形。研究認為,格式塔心理學原理有助于理解文人園林意境的生成,但在分析個人和群體的審美知覺差異方面較為不足。

關鍵詞 文人園林;審美;格式塔心理學;整體論;同型論
1 格式塔心理學的基本觀點及其啟示
1.1 基本觀點概述
格式塔心理學是西方早期心理學派之一,是 一種反 對 元 素束 捆 強調 整 體 組織的理 論 體系,由德國心理 學 家 惠特 海默(Wertheimer)、苛勒(Köhler)和考夫卡(Koffka)于1912年共同創立。惠特海默主持了似動現象實驗,指出人們總是把事物知覺為統一的整體。考夫卡在《格式塔心理學原理》中對“同型論”和“心物場” 進行了解讀,認為知覺的過程與大腦皮層的過程是同型的。場論可以被視為同型論的推論,即生理、心理現象和物理現象相對應,同樣具有完整的動力結構。苛勒的弟子魯道夫·阿恩海姆將格式塔基本理論引入審美心理研究領域,認為對藝術作品的欣賞是以主體的知覺行為為基礎的。
格式塔心理學的知覺論提出了圖形— 背景、相似、連續等知覺原則,認為腦內的力場會對片段的感覺材料進行加工,產生的認知經驗是完整的,即所謂的“完形趨向”。盡管格式塔心理學不僅僅是關于知覺的學說,但它起源于對知覺的研究,一些重要的格式塔原理大多是根據知覺研究所得到的材料推導出來的。
1.2 啟 示
受先驗論和現象學的影響,格式塔心理學家傾向于研究整體,認為整體的性質決定部分的性質,部分的性質有賴于它與整體中其他部分的關系,以及它在整體中的位置和作用。古典園林中的人工山水之所以令人產生“一峰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里”①的觀感,是因為它概括了自然山水“峭拔回環” 的整體特點,從而得到以假亂真的效果。
根據格式塔同型論原理,腦內的力場會對進入其中的感覺材料進行加工,場在自我的影響下不斷發生變化,使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知與其本身產生一定差異。中國古代的文人畫家在進行創作時,習慣從整體上把握景物的“三遠”,綜合景外鳥瞰和景內走動多重視角,收千里之景于一幅[1]。這種俯仰結合的觀察方式使得文人園林多以象征手法處理愈來愈小的場所,一卷代山,一勺代水,與建筑、花木穿插組合成意味無窮的空間[2]。加之文人常常將人生感悟、世事哲理寄托于造園、賞園、詠園的活動中,園林的審美不再是對風景的直觀反映,而是富有自省意義和非真實的再現[3],外部世界與心理場出現了同型對應。因此,從整體論、同型論的角度出發解讀文人園林,可以把握園林審美的內在規律,更直觀地理解 “寫意重于寫實”②的審美追求。
2 格式塔視角下的網師園審美解讀
網師園位于蘇州市闊街頭巷,為宋朝吏部侍郎史正志萬卷堂故址,堂前原有一座花園,名為“漁隱”。史氏既歿,其園數易主人,其中以清朝時期宋宗元、瞿遠村和李泓裔的影響最為深遠:乾隆年間,宋宗元始建網師園,又稱網師小筑。宋氏網師園僅傳一代,旋即頹圮。數年后瞿兆骙“偶過其地,悲其鞠為茂草也”,遂購此園,“增建亭宇,易舊為新”③。瞿兆骙時期的網師園賓客眾多,頗負盛名,留下了許多詩文記載。光緒年間,經李氏父子兩次填池造樓,網師園的布局已經基本與今相同。網師園布局嚴 謹,主次分明,建筑雖多而不見壅塞,山池雖小卻不覺局促,是古典文人園林中的佳構。
2.1 園的主題:審美心物場的表現
考夫卡將主體知覺到的觀念定義為心理場,被知覺的現實稱為物理場。審美活動發生于兩者結合的心物場,包含環境與自我兩個部分。文人園林創作自由,性隨主者,其審美“心物場”介于外部環境和內心世界之間,是園林環境、社會環境與個人境遇的交集。
清代網師園的第一任園主宋宗元,字魯儒,號愨庭,世 居 長洲,歷官至光祿少卿。《仲舅光祿公葬記》載,宋公“性開蕩脫略,好聲色而疏于財,樂赴人之急……官州縣族中子弟援而進者,不可敝數也。”宋宗元的灑脫性格是其“中歲抽簪”的原因之一,也使他醉心于田園之樂,樂于向眾人分享自己的園林。
“曩卅年前,宋光祿愨庭購其地,治別業為歸老之計。”(錢大昕《網師園記》)
“以太夫人年老陳情,飄然歸里。”(沈德潛《網師園圖記》)
“ 其 以 養 親 歸 也 ,有 隱 居 自 悔 之志。”(彭啟豐《網師園說》)
為了奉養母親和隱居避世,年未五十的宋宗元歸而造園。在宦海中浮沉多年的宋魯儒正如考夫卡故事中的騎馬人,一邊是現實中的太平之世——“政和民洽,大吏重之”④,另一邊則是精神上的久 居樊籠——“一執仕版,欲遂其山林之樂而不易得也”④。騎馬人自以為走過了一片大雪覆蓋的平原,度過了潛藏的危機;以宋魯儒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們則在庭園中構建了一個超然物外的隱逸世界,“循陔采蘭,凌波捕鯉……竦梧蔽炎,叢桂招隱”④,在自然山水中尋求暫時的慰藉。
“因以網師自號,并顏其園,蓋托于漁隱之義,亦取巷名音相似也。”(錢大昕《網師園記》)
“無累于中,不求乎外……園名網師,比于張志和、陸天隨,放浪江湖,蓋其自謙云爾。”(沈德潛《網師園圖記》)
“吾戚好瞿君遠村,得宋愨庭觀察網師園遺址,葺而新之,仍其故名,示不忘舊之意。”(褚廷璋《網師園記》)
“網師園”的名稱隱晦地反映了園主對統治者高壓政策的抗爭。網師,指的是結網的人,即漁父。中國傳統文學上有兩位漁父的形象:一是《楚辭》中鼓枻而歌的漁人,以截然不同的態度對待滄浪之水的清濁;二是誤入桃花源,留戀不舍的武陵漁人[4]。兩者都有反對封建專制的內在含義。宋宗元在園名中寄托漁隱的思想,沈德潛亦在《圖記》中將網師園與滄浪亭并舉,暗示兩者志趣相投。不論是宋魯儒與蘇子美思想上的共鳴,還是瞿遠村保留網師舊名的做法,都表明“漁隱”主題得到了文人群體的認可和推崇。
第二任園主瞿兆骙,號遠村,同為長洲人。瞿遠村自己動手改園,園中八景,“皆遠村目營手畫而名之”③。瞿 遠村雖無功名,但滿腹詩書,其經營園林的方式,與典型的中國文人并無二致。
“遠村于斯園,增置亭臺竹木之勝,已半易網師舊規。”(褚廷璋《網師園記》) “吳郡瞿君遠村,得宋愨庭網師園,大半傾圮,因樹石池水之勝,重構堂亭軒館,審勢協宜,大小咸備,仍余清曠之境,足暢懷舒眺。統徇舊名,不矜已力其寄情也,遠其用心也。”(馮浩《網師園序》)
“有堂曰梅花鐵石山房;曰小山叢桂軒;有閣曰濯纓水閣;有燕居之室曰蹈和館;有亭于水者曰月到風來;有亭于崖者曰云崗;有斜軒曰竹外一枝;有齋曰集虛,皆遠村目營手畫而名之者也。”(錢大昕《網師園記》)
格式塔心理學家認為,在不同的條件下,我們之所以對事物產生相同的心理經驗,是因為事 物之 間的關 系仍 然保 持 一致[5]。瞿遠村“半易網師舊規”“重構堂亭軒館”,只是在園子本身的基礎上,修繕并增添了部分建筑,對整體格局并沒有大的改變[6],且瞿氏網師園八景中有三處沿襲宋氏舊名(梅花鐵石山房、小山叢桂軒、濯纓水閣),其尊重歷史、尚友古人之心得到了世人的好評[7]。
沈德潛在《網師園圖記》中說園中“有池、有艇”,洪亮吉《網師園》詩亦稱:“他日買魚雙艇子,定應先詣網師園(圖1)。” 說明宋、瞿時期的網師園都有水門,賓客可乘游艇出入。園內空間疏朗,水體面積大,所以才有“踔爾幽賞,煙波浩然”⑤“滄波渺然,一望無際”③的現實景象,對應著 “漁隱”的審美主題。
隨著外部環境和欣賞主體的變化,審美心物場也呈現出不同的內容。同治年間,祖籍四川的李泓裔購得網師園,改園名為蘇鄰。為了滿足居住需求,封閉水門并在園東南部增建了高大的宅院。李鴻裔的改建基本形成了網師園今天的格局,水面的縮小和建筑的增多使網師園的空間變得內向而封閉[8]。這一時期,清王朝風雨飄搖,社會動蕩不安,園主客居異鄉,親朋甚少。于是 “閉門謝客,徜徉其間”⑥,網師園的詩酒宴游自此冷落。宅園之于李氏父子,居住功能大于審美意義。隨著“物理場”——現實環境的寥落,“心理場”——網師園承載的 “漁隱”主題也逐漸消隱。
2.2 造園手法:知覺組織原則的運用
知覺組織原則包括圖形—背景原則、接近性原則、相似性原則以及閉合性原則等,知覺過程具有主動性。通過知覺體驗的方式可理解到場所精神與文人園林圍繞審美主體進行意境構建的創作邏輯有內在的對應關系。因此,文人園林的造園手法可視為對知覺組織原則的實際運用。
文人園林的構景美學包括“錯綜”“虛鄰”和“幽曲”[9]等,可以看作是從不同角度調整園林中的圖底關系:“錯綜”指的是對整散、分合、斷續、虧蔽等對比關系的處理;鄰虛指的是“透氣留白”,即留足余地(背景),令景物(圖案)充分顯露;幽曲,是指通過景物的重迭來模糊圖底關系,加強園境深度,延長游覽時間。
在圖底關系明確的情況下,背景與圖形達成了一種動態平衡,顯現出整體的張力。“奇亭巧榭,構分 紅紫之 叢;層閣重樓,迥出云霄之上”⑦說的是建筑高低參差、花木色彩交輝。如圖2所示,建筑前后的灌木叢與天空是“奇亭巧榭”和“層閣重樓”的背景,凸顯出建筑物的精巧;建筑組合本身也具有圖底關系,射鴨廊半亭與擷秀樓的高低錯落形成了豐富的景物層次。
表面看來,作為背景的“底”似乎并不重要,但實際上創作者并不能拋卻這些背景直接呈現圖形,因為放棄了背景也就削弱了圖形。園林營造往往“計白當黑”,運用虛實相生的原則組織空間。《園冶·立基》有云,“筑垣須廣,空地多存”⑧,《園冶·門窗》亦稱“處處鄰虛,方方側景”⑨,認為在墻垣內外、景物之間多留余地是造景構境的前提,表達了對“底”的重視。彩霞池南北兩岸各布置了兩處建筑群組,南岸濯纓水閣面水,則北岸看松讀畫軒后退(圖3);北岸竹外一枝軒面水,則南岸小山叢桂軒后退,形成了一進一退、一實一虛的格局。倘若所有建筑都依水而建,沒有間隔退讓,沿岸空間將會顯得局促單調,缺乏變化。
阿恩海姆認為,通過重迭創造空間早已是中國山水畫的特有手法:山、水、云、樹通過重迭組成序列,建立起在縱深中的相對位置[10]。“重迭”的另一層含義,就是對“曲徑通幽”的推崇。在網師園中,“園林造景、亭臺樓閣、山水泉石的種種布置,都講究一個曲字”。一方面,這是文人園林吸收畫理,營造畫意的成果;另一方面,受現實條件所迫,私家園林大都占地較小, “不能不在螺螄殼里做文章”[9]。缺乏變化的園林建筑單體借助長廊、曲橋彼此連接,以達到無窮的境界。例如“躡山腰,落水面,任高低曲折,自然斷續”⑩的爬山廊,是佳園中不可缺少的景觀;靜止于水面上的曲橋可以增加水景層次、提供多種角度的觀賞點;走廊前的方形門洞構成了重重框景(圖4)。樓閣亭臺掩映于雜樹繁花間,曲水藏匿于石橋之后,隱隱約約,似連非連,增加了園境的深度。
知覺具有控制多個刺激并使它們形成 有機 整 體的 傾向,這種 控制規律被稱為群化原則[11]。易于被 感 知為整 體的元素通常具 有鄰近性、相似性、封閉性和連續性等特點。文人園林中的造園要素與室內裝飾元素通過形態、功能、位置等方面的 相似性、連 續性 和 鄰近 性 等 特點聯 系在一起,將豐富的文化內涵寓于空間藝術之中,構成了關于園的“良好格式塔”[12]。例 如 殿 春 簃于廳 堂 正中開 窗,將 園 林風光透入室內。花窗左右懸掛對聯,上下鑲邊,恰似一幅中堂山水畫(圖5)。這是文人園林中特有的“尺幅窗、無心畫”,模糊了室內空間與園林空間的分界,風景的相互滲透 使 室內外空間連成了不 可分割的整體[13]。
2.3 園林題詠:經驗的完形
格式塔的完形傾向是整體組織自我完成的一種動態屬性,具有兩種意義:其一,在格式塔組織未完成的時候,已經包含了一種完形的傾向;其二,已經完成的格式塔組織,也就成為簡單而具有意義的整體[14]。中國傳統文人園林中的審美主要由 “真實景象”和“題詠”兩類類外界刺激所引發,其中題詠主要包括匾額、楹聯、題刻和碑刻等形式[15]。文人園林經由題詠,溝通了審美客體和審美主體,將真實景象轉換成語言意象,從語言意象升華為朦朧意境[16],起到了閉合完形傾向的審美功能。網師園殿春簃小院入口上方的“潭西漁隱”匾額,原是網師園在史正志時期的原名,用于此處不僅點明了小院所在的方位,也暗喻庭院環境清幽,呼應了全園的隱逸主題[17]。殿春簃原址為芍藥花圃,取邵雍“多謝化工憐寂寞,尚留芍藥殿春風”為其命名,令人聯想到從前暮春時節花開遍地的景色,今昔對比,時空交錯,創造出一種“再度體驗”[16]的情境。
園林題詠所描寫的“景”,是經過腦內力場加工過的、藝術化的風景,浸潤了主體的審美情感。借用命名中對自然景物之 “形”的描畫,至“象”的生成,使其在審美意義上達到“完形”的暗示[16]。彩霞池主景——月到風來亭之名亦出自邵雍的詩句“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亭前對聯 “園林到日酒初熟,庭戶開時月正圓”,描述了月圓之際,把酒言歡的場景。題名喚起了人們心中“風”與“月”的已有經驗的圖式,形成了視覺、觸覺、聽覺等全方位的心理場的暗示,達成了心與物的同型。夜游網師園,在亭中憑欄靜觀,可見聯中之月與夜空之月、池中之月、心中之月交相輝映, “物理場”與“心理場”自然聯動,實景之中流動著清虛的意味,獲得自在玄妙的審美體驗。
相關期刊推薦:《西部人居環境學刊》是由教育部主管、重慶大學主辦,建筑城規學院具體承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型期刊。主要報道國內外室內設計學術研究成果,交流總結室內設計經驗,促進設計、生產中實際問題的解決。現設有:教學改革、名作廣場、傳統建筑、設計研究、工程實例等欄目。
声明:①文献来自知网、维普、万方等检索数据库,说明本文献已经发表见刊,恭喜作者.②如果您是作者且不想本平台展示文献信息,可联系学术顾问予以删除.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