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shí)間:2016-07-15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這篇佛教文化論文探討了“蒙古化”的藏傳佛教文化,蒙古族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領(lǐng)域受到傳統(tǒng)薩滿教文化的影響,蒙古化佛教更為明顯,富有異彩,論文闡述了藏傳佛教與蒙古薩滿教傳統(tǒng)文化的結(jié)合的宗教史,并對各種語言進(jìn)行了蒙譯。
這篇佛教文化論文探討了“蒙古化”的藏傳佛教文化,蒙古族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領(lǐng)域受到傳統(tǒng)薩滿教文化的影響,蒙古化佛教更為明顯,富有異彩,論文闡述了藏傳佛教與蒙古薩滿教傳統(tǒng)文化的結(jié)合的宗教史,并對各種語言進(jìn)行了蒙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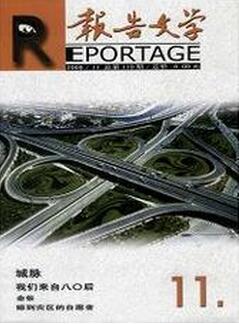
〔摘 要〕16世紀(jì)末17世紀(jì)初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qū)后,取代薩滿教成為這一地區(qū)的主流信仰,藏傳佛教文化已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占據(jù)了絕對統(tǒng)治地位,在政治、經(jīng)濟(jì)、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對蒙古地區(qū)影響深遠(yuǎn)。
關(guān)鍵詞:佛教文化論文,藏傳,佛教,“蒙古化”
16世紀(jì)末17世紀(jì)初藏傳佛教再度傳入蒙古地區(qū)以前,傳統(tǒng)的薩滿教文化駕馭著蒙古族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領(lǐng)域,蒙古人中的少數(shù)“榜式”(教師)以私塾的形式在民間教書,且沒有任何專門的文化教育場所。經(jīng)過近一個(gè)半世紀(jì)的傳播和普及,藏傳佛教已經(jīng)成為蒙古民族供奉的唯一的宗教,并在清朝的尊崇和扶植下,蒙古王公貴族和廣大蒙民篤信藏傳佛教的程度比藏族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清一代,藏傳佛教文化已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占據(jù)了絕對統(tǒng)治地位,佛教的教義經(jīng)典成為人們處理一切事情的準(zhǔn)則。“人生六七歲即令習(xí)喇嘛字誦喇嘛經(jīng)”。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祭祀祖宗或天地均離不開喇嘛。喇嘛集智慧、學(xué)問、美德于一身,是社會上深受敬仰的人們。“男女咸欽是喇嘛,恪恭五體拜袈裟”。從上層王公貴族到下層普通牧民,男子均以出家為榮。“男三者一人為僧”。所以,藏傳佛教作為蒙古多種文化淵源中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它的影響在蒙古人的心里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最終從非主流的信仰發(fā)展成主流信仰,時(shí)斷時(shí)續(xù)經(jīng)歷了幾個(gè)世紀(jì)。〔1〕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qū)發(fā)展過程中不僅吸收了薩滿教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學(xué)說,而且不可避免地帶進(jìn)了蒙古族思維模式、價(jià)值觀念、審美情趣、道德規(guī)范、性格習(xí)俗等“價(jià)值參與”,佛教的蒙古化更為明顯,富有異彩。
一、藏傳佛教與蒙古薩滿教傳統(tǒng)文化的結(jié)合。
在世界各種宗教史上,本土宗教與外來宗教在激烈的矛盾沖突中,各自變通、相互讓步,使宗教信仰多元化成為可能。世界許多地方的幾乎都發(fā)生過外來宗教傳入時(shí)與本土宗教的矛盾與沖突,這是不同文化間矛盾沖突的必然性。〔2〕16世紀(jì)末17世紀(jì)初藏傳佛教再度傳入蒙古地區(qū)后,在薩滿教之間的激烈碰撞中不僅保存了佛教在不同區(qū)域發(fā)展的共性,而且吸收了蒙古地區(qū)原有的薩滿教和其他民間信仰等傳統(tǒng)文化的成分,充分顯現(xiàn)出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qū)發(fā)展的個(gè)性。這在某種意義上佛教在西藏地區(qū)傳播和發(fā)展過程中,大量吸收當(dāng)?shù)貍鹘y(tǒng)的本教文化因素如出一轍。
薩滿教產(chǎn)生于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對祖先的崇拜,保護(hù)人及其財(cái)產(chǎn)以對付疾病和災(zāi)難造成的所有危險(xiǎn)和痛苦是薩滿教的主要功能。薩滿教承認(rèn)宇宙間的任何事物都有生命和靈魂。認(rèn)為,人的軀體是靈魂的外殼,人的生死取決于靈魂的留去,但靈魂是永生的。人死后,其靈魂到彼岸世界,與故去族人一起過著與人間無二的生活,亡者的靈魂既可保佑生者,亦可加害生者。從騰格里天神開始,經(jīng)過翁袞、先祖的守護(hù)神、布麻爾、其他已故親屬的亡靈,一直到災(zāi)難的各種人格化形式。〔3〕而薩滿教的這種思想學(xué)說一直駕馭著蒙古族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領(lǐng)域。16世紀(jì)末17世紀(jì)初藏傳佛教再度傳入蒙古時(shí),佛教教規(guī)與薩滿教的某些思想學(xué)說,即用奴隸和動物進(jìn)行血祭,供奉代表其祖先靈魂的模擬翁袞等發(fā)生了激烈的沖突,在蒙古封建領(lǐng)主的支持下薩滿教無情地被鎮(zhèn)壓,而藏傳佛教最終成為蒙古民族供奉的唯一的宗教。但是,薩滿教對蒙古族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影響并沒有因此而得到徹底消除,其主要原因之一即是藏傳佛教在傳入蒙古社會的過程中吸收了眾多深受薩滿教影響的文化因素,諸如祖先崇拜、火神崇拜、大自然崇拜等,而且其影響隨著藏傳佛教的傳播又得到了進(jìn)一步的加強(qiáng),從而使蒙古族文化具有了薩滿教、藏傳佛教雙重影響的特色。換句話說,隨著藏傳佛教的傳入和普及,清代蒙古薩滿教儀式與祝詞、咒語等有了明顯的增補(bǔ)、修改和偽裝,其辭句和形式在內(nèi)容上開始異化。
祭祀騰格里(天),最初是蒙古族薩滿教的最隆重的祭祀活動之一。藏傳佛教再度傳入蒙古地區(qū)后,這一祭天習(xí)俗被藏傳佛教繼承了下來。所祭之神,最初是祖先之神或翁袞等薩滿教的神靈,入清后又增加了藏傳佛教的佛像。另外,古老的祈禱經(jīng)文中也出現(xiàn)了佛教化的增補(bǔ)內(nèi)容。如古吉爾控噶爾騰格里原為薩滿教九十九尊騰格里天神之一,藏傳佛教傳入后它以佛教的別名大神王而出現(xiàn)在布里亞特人中間,被稱為“古吉爾騰格里鐵匠大神王”,并說它是根據(jù)佛陀圣師之尊命,由霍爾穆斯達(dá)騰格里的祝福而誕生。
祭祀敖包是蒙古族的傳統(tǒng)節(jié)日,源出于薩滿教重要的祭祀活動之一,被認(rèn)為是各種神靈的匯集處,因而倍受蒙古民眾的重視。儀式最早由薩滿主持。藏傳佛教再度傳入后改由喇嘛主持,并由喇嘛進(jìn)行祈禱和祝贊。同樣,在祭祀敖包儀式和內(nèi)容上,喇嘛教禮儀學(xué)家們或多或少對薩滿教形象進(jìn)行改造,并把地方神靈分為地神和龍神或地神龍神的八大等級。祈禱詞中明顯沾染了佛教色彩,如以神香向肯特山脈的山神奉獻(xiàn)祭祀中有了類似的祈禱:“……使暴雨、雷電和冰雹停止,使喇嘛及其初治地者運(yùn)用馱獸和坐騎的障礙消失”。〔3〕火神也是蒙古薩滿教的主要神靈之一,這一風(fēng)俗在藏傳佛教再度傳入后除了祭祀活動原有薩滿主持變?yōu)橛衫镏鞒郑从衫镞M(jìn)行祈禱和祝贊之外,火神的形象也發(fā)生了變化。
祖先崇拜是蒙古人信奉薩滿教的重要內(nèi)容。藏傳佛教再度傳入蒙古地區(qū)后,佛教僧侶們盡可能把蒙古傳統(tǒng)的祖先崇拜納入佛教體系中。在祭祀成吉思汗祈禱經(jīng)文中,絲毫不體現(xiàn)成吉思汗那種古老的狂風(fēng)暴雨之神、戰(zhàn)神和天神的特點(diǎn),而完全變成了藏傳佛教的保護(hù)神,已被看作是一尊神。一世章嘉呼圖克圖撰寫的一部祭祀經(jīng)文中,竟把成吉思汗當(dāng)成“天之愛地的梵天神”,試圖把佛教中的神僧伽婆羅與“成吉思汗的蘇勒得騰格里”考證成一體。18世紀(jì)中葉用蒙古文撰寫的一部有關(guān)成吉思汗祭祀祈禱經(jīng)文中把成吉思汗描寫道:“俯請降臨到舉行祝愿的地方,降臨到用無價(jià)之珍珠制成的御座上,降臨到用八朵芳艷的荷花制成的地毯上,非常和諧的守護(hù)神,白色信事男”。〔3〕這就是佛教僧侶們以綜合的形式把薩滿教中的古老觀念和神與佛教儀軌結(jié)合起來的典型。
藏傳佛教與薩滿教的長期對峙過程中,薩滿教在自衛(wèi)中采取了靈活的態(tài)度,開始承認(rèn)某些佛教辭句,同時(shí)也開始祈禱佛教之神,或者利用佛教符和咒而自我掩飾。同樣,藏傳佛教對蒙古薩滿教重新變得傾向于寬容起來的時(shí)候,薩滿教向一種藏傳佛教形式的過渡或異化。藏傳佛教中的一種禪師喇嘛———古爾塔木是著名的巫師,他身穿一件絲綢服裝,外套一件類似蘭色棉布女袍一樣的衣服。衣服的上部裝飾有死人的頭顱,標(biāo)志著兇教煞神,服裝的另一部分是衣領(lǐng),在佛教圣像中,它是菩薩們所固有的服飾組成部分。衣領(lǐng)上則有一種典型的薩滿教標(biāo)志———一面鏡子,背部裝飾有五色布條。五色布條與薩滿的翁袞代表著同一意義,即與惡魔作斗爭的力量。這種以成為神和巫師的喇嘛居住在寺廟中,以興奮狂舞和鬼魂附神狀態(tài)來代替驅(qū)邪薩滿。在儀式開始時(shí),古爾塔木手持鞭子煌魔刀。然后,弟子們誦讀有關(guān)此神的儀軌性規(guī)則,在鑒別神的時(shí)刻到來時(shí),古爾塔木便由守護(hù)神附身。然后,他又抓住一把劍,口中流出了帶血的涎沫,全身顫動,用劍在四周野蠻地亂劈亂砍,表示已附其身的佛教的保護(hù)神正在與惡魔進(jìn)行殊死搏斗。〔3〕這實(shí)際上是藏傳佛教僧侶們以佛教與西藏本教之爭為可循的先例,并用它顯現(xiàn)出與蒙古薩滿教中的觀念完全相同。
在清代內(nèi)蒙古東部地區(qū),類似古爾塔木神師的形式,用來代替薩滿,一般被稱為“賴清”。“賴清”不屬于任何宗教團(tuán)體,而是世俗人。他們在驅(qū)邪期間身披貝殼甲和頭戴一頂盔,以喇嘛寺院樂器中得到的鑼來代替薩滿們的鼓,并在驅(qū)邪期間口中念誦佛教祈禱經(jīng),而且正是借助于這種祈禱經(jīng)才得以控制病魔。“賴清”有男亦有女。這就是藏傳佛教對蒙古薩滿教重新變得傾向于寬容起來的時(shí)候,薩滿教向一種藏傳佛教形式的過渡或異化,也是藏傳佛教與蒙古傳統(tǒng)的薩滿教文化互動的產(chǎn)物。
二、梵、藏各種佛經(jīng)、文學(xué)、醫(yī)學(xué)、天文等著作的蒙譯。
有清一代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qū)發(fā)展過程中蒙古化現(xiàn)象的重要標(biāo)志之一就是梵、藏各種佛經(jīng)、文學(xué)、醫(yī)學(xué)、天文等著作的蒙文翻譯。
佛教經(jīng)文的蒙文翻譯始于13世紀(jì)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qū)初傳時(shí)期。由于元朝皇室崇佛,《菩薩修行化生經(jīng)》、《五護(hù)經(jīng)》、《金光明經(jīng)》、《蘇巴喜地》等佛教經(jīng)文先后翻譯成蒙文,對當(dāng)時(shí)蒙古貴族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這些著作中不同程度地充斥著佛家的理教,如搠思吉斡節(jié)兒的《佛十二撰》和《摩訶葛剌頌》等除了翻譯一些片段佛教經(jīng)典外,最重要的是開始翻譯了蒙古文版《大藏經(jīng)》(《甘珠爾》、《丹珠爾》)。16世紀(jì)后半期,三世達(dá)賴?yán)镌诿晒庞乙韨鞣〞r(shí),曾令隨行僧侶翻譯了部分《大藏經(jīng)》。為了準(zhǔn)確翻譯表達(dá)梵語,喀喇沁部的著名譯師阿玉喜固錫創(chuàng)造了蒙古文《阿里嘎里字目》,后來在他的支持下喀喇沁部的僧侶們還翻譯了其他佛教經(jīng)典。此時(shí),察哈爾部的林丹汗也意識到藏傳佛教的重要性,接受了沙爾巴呼圖克圖的灌頂,皈依了佛門,并下令翻譯108函的《甘珠爾》佛經(jīng),重新核對、整理元代以來所譯經(jīng)文,補(bǔ)譯殘缺部分。這次翻譯共召集了貢噶敖德斯?fàn)柕热嗝锖蛯W(xué)者。1629年《甘珠爾》經(jīng)翻譯完畢,并用金粉寫成。
入清以后,清朝統(tǒng)治者不僅對藏傳佛教采取扶持、鼓勵的政策,而且皇室對佛經(jīng)的蒙文翻譯尤為重視。康熙年間,在和碩親王福全主持下,烏喇特部固什畢力袞達(dá)賴等高僧學(xué)者,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奉皇帝之命將《甘珠爾》經(jīng)再次校審,匯編成108卷,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完整地木刻印刷。此后,乾隆又下令翻譯《丹珠爾》經(jīng),在章嘉呼圖克圖若必多吉的主持下,二百多名喇嘛學(xué)者共同翻譯了《丹珠爾》
經(jīng)。為了譯名的準(zhǔn)確而統(tǒng)一,將《甘珠爾》和《丹珠爾》經(jīng)的內(nèi)容提要編寫成《智慧之鑒》。同時(shí),烏珠穆沁公袞布扎布和烏喇特部固什畢力袞達(dá)賴等還編寫了蒙藏對照的《藏語便學(xué)書》。經(jīng)過七年的努力,于乾隆十四年(1749)將225卷《丹珠爾》經(jīng)全部翻譯成蒙古文。
隨著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qū)的廣泛流傳,在18-19世紀(jì),藏文在蒙古人中普遍得到使用,逐漸成為蒙古宗教語言和某些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里的學(xué)術(shù)語言。17-19世紀(jì)在蒙古地區(qū)涌現(xiàn)出幾百個(gè)藏文作家,寫下了大量的各種學(xué)科的著作。
文學(xué)方面,外喀爾喀人扎雅班第達(dá)·羅卜藏丕凌列精通蒙藏文,是杰出的翻譯家、史家和作者。他的文集中有不少詩歌。其中名為《白色水晶鑒》的訓(xùn)諭一方面闡述此世此生如何論事處世的道理,另一方面講授未來世應(yīng)做何事的教義。他還寫了一部名為《大梵天之子喜音》的由258首詩組成的詩篇,這是運(yùn)用古印度作詩理論的典范。青海蒙古巴圖特氏松巴堪布·伊西巴勒珠爾是一位博學(xué)多才的學(xué)者,幼年學(xué)起藏文和佛學(xué)經(jīng)文,寫過史學(xué)、語言學(xué)、醫(yī)學(xué)和天文學(xué)方面的諸多著作,他的文集共有8部。詩文《杜鵑美聲之歌》和《世道篇美花念珠》是其文學(xué)方面之代表作。其中,前者以比喻手法揭露了身披袈裟胡作妄為喇嘛僧人,而后者則為人們教授了今生今世如何過美好時(shí)光、人和人之間怎樣友好交往的道理,是一篇成功的訓(xùn)諭詩。察哈爾鑲白旗喇嘛羅卜藏楚勒圖木曾在多倫諾爾、北京等地研習(xí)過佛學(xué)經(jīng)典、蒙藏文翻譯等。后在察哈爾察罕烏拉廟從事寫作、翻譯和出版工作,在當(dāng)?shù)乇怀蔀?ldquo;察哈爾格卜什”而著稱。他的藏文文集有10部,其中包括史學(xué)、文學(xué)、醫(yī)學(xué)、天文學(xué)和翻譯方面的著作。
他的《名為如意寶的箴言》、《酒的弊端》等訓(xùn)諭詩,《白翁頌》等習(xí)俗詩,《對阿旺真的訓(xùn)諭》等批評僧侶腐敗現(xiàn)象的詩都很有名。他還寫過《宋喀巴傳》、《七年輕婦女的故事》等文學(xué)作品。18世紀(jì)外喀爾喀之額爾德尼召大喇嘛羅卜藏達(dá)克畢丹巴達(dá)爾杰,用藏文寫過三十多部書。其文集目錄中有不少頌詞、詩歌。阿巴噶右旗的大固什·阿旺丹丕勒,不僅是翻譯家,也是詩人。他寫的《阿旺丹丕勒之言》,以自我檢討的形式抨擊了不遵守法規(guī)、不孝敬父母、貪婪、胡說、胡作非為的蒙古喇嘛中的敗類。18世紀(jì)鄂爾多斯喇嘛羅卜藏念都克,在大庫倫出版過3部文集,其中之故事集《報(bào)應(yīng)明鏡》在蒙古地區(qū)廣為流傳。阿拉善和碩特旗喇嘛丹德爾喇蘭巴,寫過多部頌詞、訓(xùn)諭詩。其訓(xùn)諭詩中最著名的是《人與經(jīng)的喜宴》。大庫倫的堪布喇嘛阿旺海達(dá)布用藏文寫過五部二百多種文章。
其中《嚇唬老虎的老兩口》、《長毛狗策凌丕勒同班第達(dá)的舌戰(zhàn)》、《天祭》、《詞意明鏡》等文學(xué)作品揭露了僧侶封建主的腐敗,控訴社會的不平等,抨擊清朝統(tǒng)治者的沉重剝削和壓迫。
受藏傳佛教的影響,印藏文學(xué)的蒙譯工作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呼和浩特的錫勒圖固什綽爾濟(jì)把西藏佛教史上的杰出人物仲敦巴的傳記《子經(jīng)》譯成蒙文。另外,錫勒圖固什綽爾濟(jì)又把西藏詩人米拉列巴的傳記和他的徒弟達(dá)克巴多爾濟(jì)的道歌譯成蒙文。仲敦巴的師傅印度學(xué)者阿底峽的言論匯編《父經(jīng)》由衛(wèi)拉特的咱雅班第達(dá)譯成托忒蒙文;1720年西藏的佛教教義的文學(xué)作品《喻法論》及其注疏首次被譯成蒙文并版行。西藏大作家薩迦班第達(dá)·袞噶扎勒森創(chuàng)作的《薩迦格言》及其注疏多次被譯成蒙文,其中察哈爾格卜什·羅卜藏楚勒圖木的譯文和他寫的注疏很有影響。西藏的托古作品《伏藏》中之最有名的《瑪尼干布》(松贊干布王的文集)前后三次被譯成蒙文。西藏的《如意寶飾》、《魔尸的故事》等故事集,這些不僅都譯成蒙文,而且早在蒙古民間得到流傳。舉世聞名的印度英雄史詩《羅摩衍那》的部分內(nèi)容由衛(wèi)拉特人咱雅班第達(dá)、內(nèi)札薩克蒙古達(dá)云西庫固什和卻扎木措等人前后翻譯過三次;烏拉特人津巴多爾濟(jì)在他著的《水晶鑒》中引用過《羅摩衍那》的一些故事;衛(wèi)拉特人中保存的一本名為《養(yǎng)生汗傳》的托忒文本,這是至今能見到的《羅摩衍那》的最詳細(xì)的翻譯,共有8章。印度著名的佛陀傳記《故事海》由固什綽爾濟(jì)翻譯;《烏善達(dá)喇汗傳》由阿旺丹丕勒翻譯。另外,印度民間故事匯集中的主要部分也被譯成了蒙文。如《魔尸的故事》的一部分以《艷麗太陽王后傳》的名稱,在蒙古地區(qū)得到流傳;《三十二個(gè)木頭人的故事》,在蒙古地區(qū)有《畢噶爾米濟(jì)特汗傳》、《阿喇杰·布爾杰汗傳》和《苛則納汗傳》等三種本子。這些本子均源于《三十二個(gè)木頭人的故事》,但在翻譯或流傳過程中,受蒙古文學(xué)影響,有了較大的變異。
醫(yī)學(xué)方面,清代的蒙古族醫(yī)學(xué)在傳承本民族傳統(tǒng)醫(yī)學(xué)的基礎(chǔ)上,尤其是通過吸收藏傳佛教寺院相關(guān)學(xué)部醫(yī)學(xué)知識之后逐漸進(jìn)入了全盛時(shí)期。有清一代,寺院是蒙古族醫(yī)學(xué)人才成長的搖籃,寺院中對醫(yī)學(xué)教育是十分重視的。蒙古地區(qū)較著名的寺院均設(shè)有醫(yī)學(xué)學(xué)部(曼巴扎倉)。18世紀(jì),衛(wèi)拉特著名喇嘛松巴堪布·伊西巴勒珠爾在深入研究藏醫(yī)經(jīng)典《四部醫(yī)典》和印度醫(yī)學(xué)巨著《醫(yī)經(jīng)八支》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傳統(tǒng)的蒙醫(yī)學(xué)和臨床實(shí)踐,撰寫了著名的蒙醫(yī)學(xué)著作《四部甘露》和《認(rèn)藥白晶鑒》。《四部甘露》系蒙醫(yī)學(xué)基礎(chǔ)理論的經(jīng)典著作,著名的蒙醫(yī)學(xué)“六基論”理論即來源于此書。方劑學(xué)著作有占巴拉用藏文寫的《方海》(又稱《蒙醫(yī)金匱》)收有一千七百余單方,二千余配方;烏珠穆沁公袞布扎布著《各種重要藥方》(蒙文本),所收驗(yàn)方分102個(gè)專題;高世格著《普濟(jì)雜方》
(蒙文本)所收單方和驗(yàn)方均以蒙漢藏滿四種文字合壁對照寫成。診斷學(xué)著作有羅卜藏蘇勒合木著《蒙醫(yī)制劑和脈診》
(又稱《脈診概要》)重點(diǎn)論述了脈診學(xué)原理。此外還出現(xiàn)了方便實(shí)用的《脈訣》、《號脈便覽》等著作。藥物學(xué)著作中除了伊西巴勒珠爾的《認(rèn)藥白晶鑒》之外,羅卜藏蘇勒合木的藏文著作《本草分類》、占巴拉多爾濟(jì)的《蒙藥正典》等有較大的影響。另外,喇嘛醫(yī)生們譯著了諸多藏醫(yī)著作。如《蒙藏合壁醫(yī)學(xué)》、《醫(yī)學(xué)大全》等等。
天文學(xué)方面,藏傳佛教寺院五大學(xué)部之一的洞闊爾學(xué)部(時(shí)輪學(xué)部)專門研習(xí)天文、歷法、星占學(xué)。由于規(guī)模較大之寺院均設(shè)有時(shí)輪學(xué)部,使這一機(jī)構(gòu)中傳授和學(xué)習(xí)時(shí)輪學(xué)的喇嘛成為蒙古地區(qū)研究和培養(yǎng)天文歷算學(xué)的專門人才。衛(wèi)拉特著名喇嘛松巴堪布·伊西巴勒珠爾作為蒙古地區(qū)的著名的珠爾海家,不僅在寺院里主持過時(shí)輪學(xué)部,還于嘉慶四年(1799)建立過專門研究珠爾海的機(jī)構(gòu)“珠爾海學(xué)塾”。他寫的歷算方面的著作是《漢歷概要》、《算學(xué)明鑒、歲月計(jì)算新法》均由藏文寫成,并廣泛流傳于蒙古地區(qū)。隨著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qū)的進(jìn)一步傳播和發(fā)展,藏歷紀(jì)年在清代越來越多的被蒙古人所采用。
三、蒙古語誦經(jīng)對傳承和發(fā)揚(yáng)蒙古族傳統(tǒng)文化的作用。
有清一代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qū)發(fā)展過程中“蒙古化”現(xiàn)象的另一重要標(biāo)志之一就是蒙古語誦經(jīng)儀式的產(chǎn)生。
16世紀(jì)后半期藏傳佛教再度傳入蒙古時(shí),喇嘛或寺院的誦經(jīng)儀式僅僅使用藏語誦經(jīng),尚未產(chǎn)生蒙古語誦經(jīng)這種特殊現(xiàn)象。蒙古語誦經(jīng)儀式的產(chǎn)生與藏傳佛教高僧內(nèi)齊托因的傳教活動有密切的聯(lián)系。內(nèi)齊托因是衛(wèi)拉特蒙古土爾扈特部貴族墨爾根特穆納之子,大致生活在1587年至1653年之間。1607———1619年期間他到西藏扎西倫布寺,在四世班禪指導(dǎo)下學(xué)習(xí)佛教經(jīng)文,學(xué)成之后赴內(nèi)蒙古地區(qū)傳教。他在呼和浩特附近的大青山山內(nèi)修行時(shí),曾到呼和浩特參加那里舉行的大召法會,因內(nèi)齊托因用蒙語誦金剛經(jīng)而遭到大召喇嘛們的非議。17世紀(jì)30年代,薩滿教“翁滾”盛行的內(nèi)蒙古東部的科爾沁等部蒙古人之所以最終皈依藏傳佛教,與內(nèi)齊托因的用蒙語傳法有直接的聯(lián)系。受內(nèi)齊托因蒙語傳法或蒙文誦經(jīng)之影響,內(nèi)札薩克蒙古哲里木盟科爾沁右翼中旗的巴音和碩廟、昭烏達(dá)盟巴林右旗的特古斯布日德勒圖寺、阿魯科爾沁旗的赫西格西圖格齊寺、扎魯特旗的格根廟、察哈爾的察罕烏拉廟、烏蘭察布盟烏拉特旗的梅力更廟、呼和浩特的小召、外扎薩克蒙古莫爾根王旗的浩尼齊廟、圖謝公旗的畢力宮寺、北京的黃寺等寺廟在舉行各種法會時(shí)全部用蒙文誦經(jīng)。據(jù)統(tǒng)計(jì),在內(nèi)外蒙古蒙文誦經(jīng)的寺廟共計(jì)64座。〔4〕以蒙文誦經(jīng)的蒙古地區(qū)寺廟中,烏拉特旗梅力更廟最為典型。在近二百多年的歷史當(dāng)中,該寺比較完整地傳承了蒙古語誦經(jīng)的誦經(jīng)體系。梅力更廟的蒙古語誦經(jīng)經(jīng)過了從“老誦經(jīng)法”到“新誦經(jīng)法”的發(fā)展階段。〔5〕“老誦經(jīng)法”是通過初創(chuàng)者內(nèi)齊托因及其弟子梅日更格根一世鼎瓦喇嘛以及經(jīng)師烏古里袞達(dá)賴、諾們達(dá)賴、丹畢堅(jiān)贊等高僧的努力下形成的。
其特點(diǎn)是經(jīng)文的翻譯過多地局限于原文詞句,逐字逐句的機(jī)械翻譯造成了譯文接近于長篇文章的形式,缺少詩律特征,誦經(jīng)韻調(diào)基本運(yùn)用原有的藏文誦經(jīng)韻調(diào),經(jīng)文與曲調(diào)不協(xié)調(diào),尚未形成適合與蒙古語經(jīng)文的具有相對獨(dú)立特點(diǎn)的誦經(jīng)韻調(diào)。“老誦經(jīng)法”雖然有不足之處,但在它的形成過程中基本完成了藏文經(jīng)典的翻譯工作,并且將其運(yùn)用到了實(shí)際的誦經(jīng)儀式中,實(shí)現(xiàn)了蒙古語誦經(jīng)儀式的初期模式,為“新誦經(jīng)法”的產(chǎn)生奠定了基礎(chǔ)。
蒙古語“新誦經(jīng)法”的徹底完善是在三世梅日更格根羅桑丹畢堅(jiān)贊時(shí)期。他翻譯、編著大量的經(jīng)文以及世俗詩詞、歌曲之外,還著有三十三章《黃金史》、《梅日更格根醫(yī)方》、《陰山藥物》等重要?dú)v史和醫(yī)學(xué)著作。他還根據(jù)蒙古薩滿教經(jīng)文撰寫了《伊孫蘇力德騰格里音桑》、《圣祖成吉思汗桑》、《百老翁桑》等大量的儀軌文使用于各類佛教儀式中,并根據(jù)本寺“查瑪”樂舞,于1750年編寫了《鉆石》一文,詳細(xì)闡述了蒙古“查瑪”樂舞的表演意義和詳細(xì)的表演步驟。尤其是他與經(jīng)師諾們達(dá)賴合作,在已有佛教經(jīng)文的基礎(chǔ)上,對照梵文、藏文經(jīng)典翻譯成蒙古文經(jīng)典,將翻譯后的經(jīng)文統(tǒng)一為具有嚴(yán)格格律的詩歌形式重新創(chuàng)作、配置了誦經(jīng)韻調(diào)和模式,使得蒙古語誦經(jīng)更加符合蒙古語言的特點(diǎn),與原有的“老誦經(jīng)法”相比有了明顯的改進(jìn)。“新誦經(jīng)法”的主要特點(diǎn)在于將佛經(jīng)譯文規(guī)范為詩歌形式加以嚴(yán)格的格律化,重新創(chuàng)作編配了誦經(jīng)韻調(diào),實(shí)現(xiàn)了經(jīng)文與誦經(jīng)音調(diào)的完美結(jié)合。這種具有蒙古音韻的格律化佛經(jīng)誦經(jīng)方法,既有利于幾十個(gè)甚至幾百個(gè)喇嘛同時(shí)誦經(jīng)的節(jié)奏,又便于不識字喇嘛們背誦長達(dá)幾百幾千行的佛經(jīng)。〔5〕總之,蒙文誦經(jīng)的格律特點(diǎn)雖然受到印、藏詩歌格律的影響,但由于蒙古語言文字自身的特點(diǎn)以及羅桑丹畢堅(jiān)贊所創(chuàng)誦經(jīng)韻調(diào)的獨(dú)創(chuàng)因素,使得傳承至今的蒙古語誦經(jīng)在諸多方面與藏語誦經(jīng)有很大的區(qū)別。這不僅對傳承蒙古族傳統(tǒng)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而且通過蒙古文誦經(jīng),佛教的蒙古化更為明顯,富有異彩。
〔參考文獻(xiàn)〕
〔1〕烏力吉巴雅爾。蒙藏文化關(guān)系史大系·宗教卷〔M〕。北京: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2001:288.
〔2〕丁守璞,楊恩洪。蒙藏文化關(guān)系史大系·文化卷〔M〕。北京: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2000:156.
〔3〕〔德〕海希西。蒙古宗教〔A〕。蒙古史研究參考資料(32-33輯)〔G〕。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大學(xué)蒙古史研究所。
〔4〕色·嘎拉魯。蒙傳佛教佛經(jīng)文化藝術(shù)史(蒙古文)〔M〕。呼和浩特:
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1064.
〔5〕包·達(dá)爾汗。羅桑丹畢堅(jiān)贊與蒙古語誦經(jīng)儀式〔J〕。內(nèi)蒙古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6,(5)。
推薦期刊:《報(bào)告文學(xué)》湖北省新聞出版局主管、長江文藝出版社主辦的刊物,主要欄目:研究報(bào)告、文獻(xiàn)綜述、簡報(bào)、專題研究 。